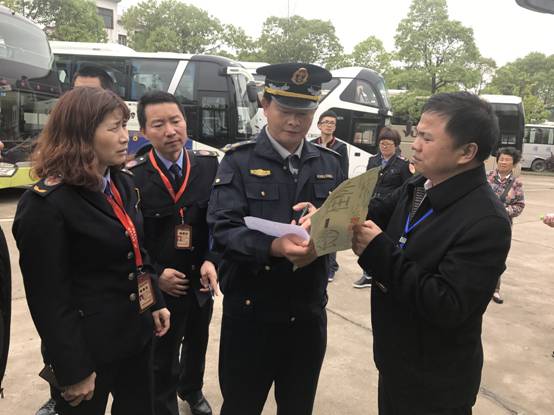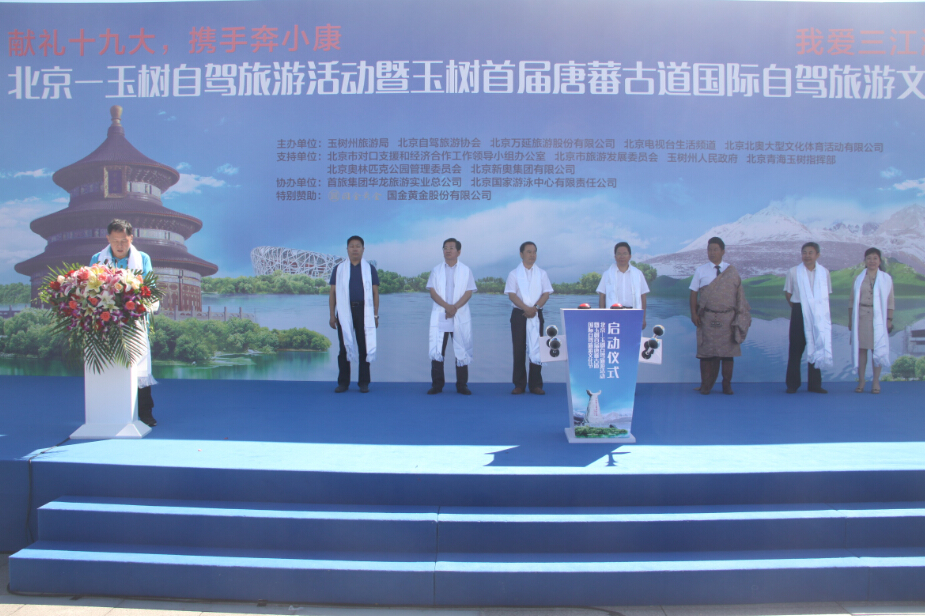近年来,乡村游几乎成了各地振兴乡村经济的产业标配。无论是以精准扶贫为目的的地方政府,还是急于寻求投资新风口的工商资本,都对这一新兴领域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去年下半年,国家十二部委联合启动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计划,全国超过2万个村被列为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其中,我省分配到472个名额。3月底,福建乡村旅游扶贫“春季攻势”行动在长汀县启动。
回顾国内乡村游并不算长的产业发展史,无法否认的是,其在改造村庄面貌、培育农村产业方面,的确颇有建树。但纵观国内的乡村游案例,唱大戏的更多是行政与资本,本土乡民的角色显得弱化。
回溯各地推行乡村游经济的初衷,除了源自消费理念的革新与市场需求的变化,更多是为了给乡村发展注入新动能,使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创业就业,让因劳动力转移而出现凋敝的乡村“复活”。此外,本土乡民本身就是乡村游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文资源。数千年来活态传承的人居方式、劳动场景、饮食文化、古法工艺、民俗风情,构成了乡村的独特性格与风貌,是最富有人情味的乡村景观。
一个理想的乡村游发展格局,应当是本土乡民充分认同并积极参与,在与政府、社会资本、游客等角色多元互动的过程中,释放内生动力,复兴乡村经济,实现乡土再造。作为村庄的内生动力,村民在乡村游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然而,不少村民对乡村发展的理念与前景缺乏认同,市场意识尚未觉醒。在发展乡村游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尴尬情景。早前,福建省旅游局在全省确立了11个闽台乡村旅游合作试验基地,并出资聘请台湾专家编制发展规划。当时,台湾乡村旅游协会曾3次到访长泰县陈巷镇山重村与后坊村,计划走村入户,对村庄的资源进行全方位的调查,对村民一对一地进行产业辅导,却因为村民不理解、不配合而难以开展。尽管台湾团队最后还是拿出了一份较有创意的规划书,但因为村民实施意愿低,最终被束之高阁。
此外,即便是有意愿参与乡村游开发的村民,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被边缘化的困境。近年来,大量工商资本下沉到农村发展乡村游项目,却忽视了开发者与原住民之间的利益协调。百姓被从古民居中驱离,无法从旅游开发中获取适当红利,进而滋生矛盾甚至冲突,此类现象并不鲜见。发展乡村游固然需要资本的支持,但乡村游不能简单套用规模经济的逻辑,其背后应有更多社会效益的考量。更何况,原住民的充分参与,确实能成为让乡村游产品更具有人情味、更能打动人心的力量。
因此,发展乡村游,应当理顺政府、企业与本地村民之间的关系,强调后者的主体地位。
作为乡村游经济的引导者、协调者与监管者,地方政府的首要责任在于培育村民的市场意识,激活、培育和保护村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云霄县和平乡致力于依托当地根基深厚的枇杷产业发展乡村旅游,乡党委书记方艺强描述了这样的场景:“为了招徕潮汕地区的游客,村里一名50多岁的妇女,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潮汕方言。村民自发地积极开发各类特色产品,薏米水、枇杷叶茶、菊花茶等纷纷出现在游客面前。”对于这样看似粗放实则充满活力的商业形态,即便要考虑将其纳入规范的经营框架,也应充分保护村民原生态的活力。
对于村民发展能力欠缺的现状,云霄县下河乡内龙村的返乡创业者引入了社区营造的经验,同样有启发意义。他们挖掘本村年轻骨干力量,让其在修复家乡土楼、发展生态农业、整治乡村环境、接待国内外志愿者、外出学习、妇女互助创业的过程中,接受新理念,掌握新技能,试水乡村旅游,以期最终带动全村的发展。
拓宽村民在乡村游经济中的参与渠道,同样重要。这个过程中,政府应重在引导社会资本,以项目带动村民致富,促成资本与村民有效互动。南靖县南坑镇新罗村便正在探索村民入股与企业投资相结合的开发方式。按照计划,全村将有超过500人,以古厝、土地等资源要素入股,参与乡村游项目开发。这既有助于提高村民参与度,又能有效协调村民与企业的利益关系,保证村民的话语权与收益权,真正实现社会资本抽得回、乡村发展带不走。
需要强调的是,主张村民在乡村游开发中的主体作用,不等同于排斥政府与社会资本参与。缺乏政府的引导与监管,未明晰开发与保护的界限,乡村游便可能掉入过度商业化、同质化、无序失范的陷阱;缺乏外部资源的导入,乡村游经济将心有余而力不足,推进乏力。一个理想的乡村游发展路径,应当是以村民自治与参与为核心,多方互动,和谐互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