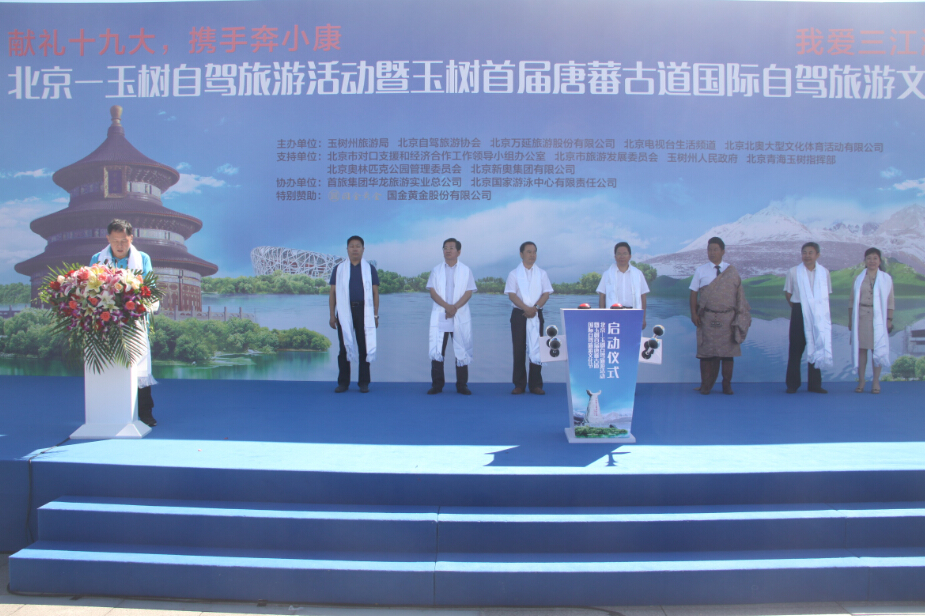导语:何不转换一下时空,去找你的“诗和远方”,以及,一个不同的自己、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们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房子,但却失去越来越多的家园。”
急匆匆的社会时代,人们的心乱了,也越来越焦虑了,更甚是找不到让自己的心安的原乡了。轻松吟唱着“诗和远方”,却从没想过“诗和远方”是什么,在哪里。日常生活中,“苟且着,偶尔抬起头来仰望星空”,只是偶然梦中出现的一幕美好的画面,是否又想过用心去追寻呢?
“闲时白天看云彩,夜里数星星,看花开花落,过过云舒云卷悠然的小日子。”
对于《新周刊》创办人孙冕来说,他的“原乡”是云南,他的“梦”就是梦蝶庄。他在丽江的玉龙雪山脚下束河古镇中、大理古城旁分别造了一座“梦蝶庄”,初衷就是找一个自己喜爱的地方,便于三五老友相聚,“闲时白天看云彩,夜里数星星,看花开花落,过过云舒云卷悠然的小日子”。

取名为“梦蝶”,出自孙冕在登珠峰途中所做的一个梦:晨曦中,花儿动了起来,一群群地集结,最后化成七彩蝴蝶,重重叠叠绕着太阳盘旋……无意中,他跟几千年的逍遥老头庄周一样,做了同样疯狂且斑斓的梦。“人与清风明月同在,悠然如庄周梦中之蝶,逍遥天真,真得雅趣,物我两忘,不以世事撄心。这不就是梦蝶庄所要承载的生活状态么!”
所以孙冕这样发出邀请:“来哦,在小庄还可梦梅、梦柳、梦竹、梦菊、梦溪……”
目前,孙冕正在张家界筹办第三家梦蝶庄,请来台湾建筑师姚仁喜担任总设计师。孙冕亲手写下“张家界梦蝶庄三大法则”:一、构建全球社会文化精英生活部落;二、体验世界遗产,感受大自然的精、气、神;三、修复心灵和身体健康的第一居所。
“凌晨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
现代人对旅馆的理解,不外是床铺干净、隔音良好、Wi-Fi畅顺——对一个“过夜的地方”又能有多少奢求?但旅馆不应该仅仅是一个“过夜的地方”。好的旅馆,追求的是“来者如归”,让来客把旅馆当成自己的另一个家。
把“来者如归”四个字挂在墙上的京都柊家,就是让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留恋的“家”。川端康成在柊家指定住14号房,他曾描述住在这里的感受:“京都,一个细雨的下午,我坐在窗畔,看着雨丝丝落下,时间仿佛静止。就是在这里,我清醒地意识到,宁静这种感觉,只属于古老的日本。”
而川端康成在旅馆写过的最美的文字,当属《花未眠》一文中这一句:“凌晨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当时,他下榻热海一个旅馆,过于劳顿的他早早入睡。凌晨醒来,他才发现了房间里的海棠的美。由此,他开始思考一些严肃的美学问题。他把自己的思考归结于“独自住在旅馆里,凌晨四时就醒来”。

有人说,在丽江梦蝶庄,也可以仿写川端康成的诗意:“丽江,一个晴朗的下午,坐在餐厅,看着玻璃房顶外核桃树银色的枝桠伸向天空,时间仿佛静止。就是在这里,让人清醒地意识到,宁静这种感觉,大概只属于雪山下的这片宅子。”
编剧宁财神说,在梦蝶庄最大的享受是晒太阳。“经常会在阳光下昏睡,直到衣衫被晒得发烫,醒来时,浑身充满力量,像被高手补了一道真气,随时准备蹿上墙头,仗剑四顾,击退数百强敌,然后仰天长啸:老子要辞职,断网,关手机,从现在起,凡尘俗事,通通去死。”导演高群书则说:“如果你在梦蝶庄梦不见蝶,要不是你没喝高,就是因为你身边卧着一只蝴蝶。嘘,那只蝴蝶怕冷。”
“人活着便是在路上,要么醒来要么睡去,睡着了,或许还有梦。”
在旅馆,你可以写作,像阿加莎·克里斯蒂、海明威、川端康成、纳博科夫等作家那样。
在伊斯坦布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在佩拉宫的411房里写出《东方快车谋杀案》;在哈瓦那,海明威在“两个世界”旅馆的511房用独特的“站着写作”的方式完成《丧钟为谁而鸣》,他赞誉这里是“非常适合写作的地方”。
在旅馆,你也可以像杜拉斯那样恋爱。
在特鲁维尔的黑岩旅馆,杜拉斯和比她年轻50岁的扬·安德烈斯一起生活在大海的边缘:“我们很孤独,我们周围是浪涛声,孩子们的喧哗声,还有炎热……”他们写作、恋爱,她写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扬·安德烈斯》,他则写出一生中唯一一部作品《我的情人杜拉斯》。

在旅馆,你可以写作,可以恋爱,更重要的是你还可以晒着太阳做着梦。
家,就如在一个好旅馆如梦蝶庄,你可以尝试很多种可能性。演员喻恩泰如此理解“家”:不是特指一所房子,而是一种心境,心安的地方便是家。对他而言,梦蝶庄就是这样一个“家”,让他心安且喜悦。
“人活着便是在路上,要么醒来要么睡去,睡着了,或许还有梦。”